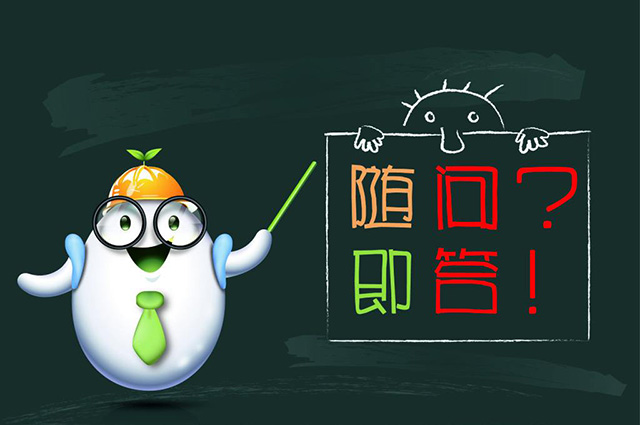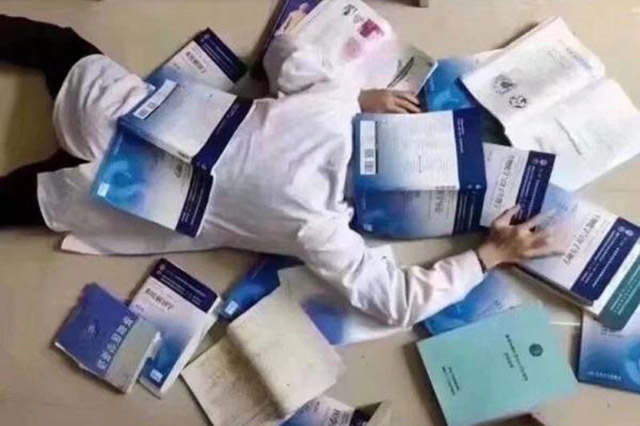为什么人不能“机”心太重?庄子用三个经典故事讲透人生大智慧,读懂你离成功不远了

酷暑时节,西子湖畔,“神机妙算:世界织机与织造艺术”正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如火如荼地展出。“前言”开篇引英国已故中国科技史权威李约瑟的话说:“在中国古代汉语中,机不只是指织机,而且指机智以及智慧。”将“机”指纺织机(loom),而有别于西方码头的起重机(crane),成为中国农桑文明与西方商业文明本质上的差异。这是李约瑟在为德国迪特·库恩《中国科学技术史·纺纱卷》一书所写的序言里提出来的观点。
但这很值得商榷。30年前,与李约瑟这篇序同时,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李志超先生认为,“机”最早应指“弩机”。就功用而言,“机”就更具体而微了,是控制驽、弓等发射的机关所在,小而紧要,一剑封喉。对此,东汉许慎《说文解字》解得明白:“机,主发者也。”《尚书·太甲上》更直言:“机,弩牙也。”后来,“机”从主宰机械势能、潜力发射的部件引申到所有机械,织机仅是其中之一;同时,沉淀于其中的“见微知著”“用小制大”的信息论、控制论思想,更造就了东方有为进取的伟力和智慧!
飞机、手机、计算机,机遇、机智、占先机,机要秘书、机关部处、机密文件,相机行事、随机应变、神机妙算……我们每天都在说“机”、用“机”,但“机”的源流和内涵却早就淡出普通大众的视野了。
机,是中国古人仰望星空、内省道德的一个独特视角。庄子非但不例外,而且特别重视其科技与社会隐喻,并分别以寓言、重言和卮言三种写作风格,从“机”眼三窥于“道”。
“机巧忘夫人心”与载道的根本
很多人对老庄“小国寡民”“绝圣弃智”这种向后看的历史观不理解。也许,《庄子·天地》中的一则寓言——即虚构与委托的故事能让人有所领悟。
话说子贡出使楚国返回晋国,途经汉水南岸,偶遇一位老者正在浇灌菜园。只见老者挖通地道,抱起陶瓮,下到井口,灌满井水,再抱着陶瓮颤巍巍地将水倒到地沟缝里。子贡见老者实在艰难,上去边帮忙边建议:“我给您推荐一种机械,一天可以浇百区之田,又省力又高效,您不想试试吗?”老者不解,仰头问道:“有何见教?”子贡扬声说:“将木头凿成汲水的机械,后重前轻,一俯一仰,抽水上来,哗啦流淌。这就是桔槔。”
子贡出于好心,未曾想却招来一顿教训。老者先是愤怒,随后笑道:
“吾闻之吾师,有机械者必有机事,有机事者必有机心。机心存于胸中,则纯白不备。纯白不备,则神生不定;神生不定者,道之所不载也。吾非不知,羞而不为也!”
在老者看来,子贡是在给他挖坑:机械可以省却人工,但又让人做事取巧;取巧耍滑形成习惯,内心就会不再纯白;内心不再纯白无邪,就会心浮气躁不安;空明的心充满浮躁,就不能再感知大道。我并非不知道你那劳什子的“桔槔”,而是我羞于用它!
从“机械”到“机事”,从“机事”到“机心”,从“机心存胸”到“纯白不备”,从“纯白不备”到“神生不定”,从“神生不定”到“道之不载”……层层递进,一气呵成。一句话,机巧让人迷失天性!
关于“用力甚寡而见功多”的省力机械——桔槔,庄子多有提及,如《天运篇》:“且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?引之则俯,舍之则仰。彼,人之所引,非引人者也,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。”是说,机械只是工具,是人的应用而非工具本身,变革了人的精神。
老者一席话,让能言善辩的子贡惭愧无比,低头不语。在得知是孔子的高足后,老者又对子贡进行了新一轮的敲打:“你看你刚才,失魂落魄、六神无主的样!自身都治理不好,还有空治理天下吗?你该干嘛干嘛去,我还忙着呢!”
果然,子贡听后,愈加惭愧,神色骤变,以至怅然若失无法自持。走出30里外,方才恢复常态。老者的话,彻底颠覆了子贡的三观!原来在他心目中,天下只有老师孔子一位圣人,未曾想浇菜园子的老者一点也不差。孔子常训导说:做事可行,功业求成,出力小而功效大,这才是圣人之道。而这位老者却教给他完全相反的道理。
本就聪明的子贡,很快有了新的感悟:“执道者德全,德全者形全,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,圣人之道也!”这一段环环相扣、前呼后应的警句,既是对其师孔子说教的反叛,也是对之前老者教诲的反思!由此,子贡得出“功利机巧,必忘夫人之心”的千古高论,即功利机巧必然不会放在有道者的心上!
园圃老者认为保全精神就是保全道德,远离机巧返璞归真才能真正成就大道。不然,世风日下,人心不古,个个心浮气躁,都去钻营投机,不肯踏实做事,这样,世界还成其为世界吗?庄子认为,上古时期,君王虽在位,却无心治世,效法天道,无为而治,百姓也淳朴率真,天下由是承平;及至黄帝以后,有为而治,并以仁爱、忠义规诫百姓,奸猾之习大兴,社会堕落不已。对“相呴以湿,相濡以沫”的“仁义”,庄子认为那是环境恶化后的无奈之举,艰难困顿不说,还难以为继,“不如相忘于江湖”,即回归自然——江湖之中,鱼儿自然会忘掉脆弱甚至虚伪的“仁义”!所以,“仁义”不过是统治者借“圣人”之名强加于民的“心网”。庄子大声疾呼:“圣人生,而大盗起!”“圣人不死,大盗不止!”由此,老庄主张“绝圣弃智”“不尚贤,使民不争”,回到从前。
“非淡泊无以明志,非宁静无以致远。”这句话,对以出世的“道”的诸葛亮形象是适用的,但对以入世的“儒”的诸葛亮身份就不妥当了。出世,意味着“功名”。“功”者,外在诱惑也,何以“淡薄”?“名”者,内心欲望也,何以“宁静”?前提不在,何谈“明志”和“致远”?这是儒家在逻辑上的困境。
与这则寓言相呼应,《论语•微子》有一段真实的隐者与孔子的对话。楚国狂人接舆将孔子比作凤凰但又为之不值,长沮、桀溺也是这样看的。“滔滔者天下皆是也,而谁以易之?”按照道家、隐士的观点,历史的衰微和时代的堕落犹如江海横流,没人能够阻挡;而在出世的儒家眼里,情形有所不同,恰如孔子所云:正因为天下无道,我才想以我之道去变革天下之无道。如果天下有道,也用不着我孔丘去劳神费心、东奔西走了!
看来,孔子的历史观与老庄并无二致,不然也没有“礼崩乐坏”的悲叹了。只是孔子竭力以“仁义”之“道”去变革风气日下的现实社会。老庄则不然,认为“仁义”既是社会衰微的结果,也是历史退步的渊薮!从而主张回归“小国寡民”的上古社会。
我们为孔子的执着感动,更为庄子的智慧叹服。现实中,被小聪明害惨害死的人不知凡几,庄子笔下那只灵巧的猴子不就是因为卖弄聪明而丢了性命吗?可悲的是,许多人到死都不知是被什么所累所害。保持内心的纯净平和,不为外界的诱惑所扰,大巧若拙,大智若愚,“功利机巧,必忘夫人之心”,方能保身全生、养亲尽年。
“机缄而不得已”与得道的路径
庄子认为“机械”、“机事”会生“机心”,使人“纯白不备”、“神生不定”以至“道之不载”,这是否意味着庄子反对人们去认知和把握“机”呢?
《天运篇》中,庄子用重言即重述与援引的形式,虚拟了“有人”与卜者巫咸祒的对话:
“天其运乎?地其处乎?日月其争于所乎?孰主张是?孰维纲是?孰居无事,推而行是?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?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?云者为雨乎?雨者为云乎?孰隆施是?孰居无事,淫乐而劝是?风起北方,一西一东,有上彷徨,孰嘘吸是?孰居无事,而披拂是?”
数行之间,14个问题,字字珠玑,句句精绝。特别是五个“乎”字,文笔恣肆,想象瑰奇,哲理深刻,气魄恢弘,比之后来屈原的《天问》,精简许多,生动许多。
吊足了胃口,还是不知问道者为何人,只好留待人们去想象。无疑,问道者绝非泛泛之辈。看,日月经天唤作争,所言如人相追夺;主张、维纲,乃着力之意;机缄不得已,运转不自止,言自主而不由他;至于天气下降、地气上腾,自然为云为雨,但不知是云为雨还是雨为云?如此设问,奇特万分……特别是“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”一语,点破天地运行、万物变化一定有“机”在背后起着作用。这样,“机”就等同于庄子心目中的“道”,有规律和法则之意了。
对于以上纯以自然为题的设问,卜者巫咸祒不仅答非所问,而且统而化之:“天有六极五常,帝王顺之则治、逆之则凶。九洛之事,治成德备,监照下土,天下戴之,此谓‘上皇’!”既天人相分,又天人合一,有如后来荀子基于“天行有常”的“疆本而节用,则天不能贫;养备而动时,则天不能病;循道而不忒,则天不能祸”的有为进取的自然观。天的运行自有规律,与人无干,但人必须遵从天的规律,即“天道”,也就是缄默于天地自然深处的“机”,如此,方能“制天命而用之”。这里的“天命”,朱熹注为:“天道流行之自然也。”本质上就是自然之“机”。
我们试着将以上问答提炼成诗:
“天运地处日月争,谁作主张谁维纲?机缄宇宙自推行,顺之莫逆世事昌!”
庄子非但不反对对“机”的领悟和驾驭,相反认为只有认知了“机”,把握住“道”,人才能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,迈向自由王国的彼岸,优游地生,快意地活,自由翱翔,纵情歌唱,“上与造物者游,而下与外死生、无终始者为友。”这就很有点康德为自然界立法的味道了。为此,庄子创作了庖丁解牛、痀偻承蜩、吕梁丈夫、削木为鐻、津人操舟以及轮扁斫轮等汪洋恣意的寓言故事,并由此诞生了“目无全牛”“游刃有余”“踌躇满志”“善游忘水”“不徐不疾”“得心应手”等脍炙人口的成语。这些寓言故事,也解答了认知、把握“机”(得道)的要领——纯白之心、虚静之道,以及路径——持恒生质变、忘物而无我、自在又逍遥。
一名叫丁的庖工解牛十九年,解牛不下数千头,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,官知止而神欲行”,进入忘了全牛、入定无我之境,以无厚入有间,恢恢游刃有余。得解牛之道的庖工,踌躇满志,将艰辛的劳作变成一种艺术、一种快乐,手触、肩靠、脚踩、膝顶,哗哗作响,纹丝不乱,活脱脱踏着古乐节奏的一场舞蹈秀!
每年五、六月间,驼背老人都要用竿头顶迭丸的方法苦练捕蝉本领,“累丸二而不坠,则失者锱铢;累三而不坠,则失者十一;累五而不坠,犹掇之也。”捕蝉时,老人心无旁骛,眼中只有蝉的翅膀,用竿粘蝉就像捡一样!孔子不由赞叹:“用志不分,乃凝于神。”得粘蝉之道的老人从容而自信:“何为而不得?!”
对于生于水、长于水的吕梁男子来说,水是习性、本能和生命。“与齐俱入,与汩偕出”,顺着水的流势出发、顺着水的性质起伏,“从水之道,而不为私”,激流险滩,畅游无阻,“不知吾所以然而然”,完全是一种顺应自然的本能行为。得游水之道的男子是快乐潇洒的,“数百步而出,被发行歌,而游于塘下。”
一名叫庆的木匠在用木头制作钟鼓之前,一定要斋戒七天,去除功名利禄、是非美恶之心,最终忘却自己还有四肢形体,达到忘物而无我之境。期间,排除外界纷扰,专注于工艺。然后,入山林,观天性,以天合天,择取外形、质地与钟鼓之声最和谐、最共鸣的木材。这样,钟鼓之声才能鬼神皆惊。
庄子其他的寓言故事,如津人操舟,说明忘水无我,即祛除精神上的外在累赘,对善游者学习驾船的下意识激励;又如轮扁斫轮,说明不疾不徐才能得心应手,“有数存焉”,通达于道。
通过这些寓言故事,庄子生动地阐释了只有忘物无我、无欲无为,才能“依乎天理”,顺应自然,认知并掌控“机”,无惧无忧,超越生死,实现养生悠游、自在逍遥的得道人生。所以,庄子“机缄而不得已”的自然观及其得道之法正是其“机巧忘夫人心”的人生观的有机展开,二者是一体两面、一枝两杈的关系。
“万物出入于机”与顺道的情怀
顺应自然,无欲无为,以无“机”之心领悟和把握“机”,从而获得生命的力量和精神的解放!反过来,结果蕴含在前提之中,于是,这个力量,这种解放,也具有顺应自然、无欲无为的意蕴。也就是说,这个力量是和平、仁爱的,这种自信是宽容、利他的。无为而无不为,无不为而无为,很趣味,很辩证,是大智慧。
《至乐篇》中,庄子以卮言即直抒胸臆的风格将上述思想形象化了:
“种有几,得水则为㡭,得水土之际则为鼃蠙之衣,生于陵屯则为陵舄,陵舄得郁栖则为乌足。乌足之根为蛴螬,其叶为胡蝶。……羊奚比乎不箰,久竹生青宁;青宁生程,程生马,马生人,人又反入于机。万物皆出于机,皆入于机。”
胡适认为,庄子试图“把一切生物都排成一本族谱,从极下等的微生生物到最高等的‘人’,一步一步的进化”。“几”是“机”的抽象,“机”是“几”的具化。“几”字古为“幾”,构词中的“丝”意为“胚芽”,细小而须兵守(“戍”),故精微而关键,由此成为“见微知著”“用小制大”的方法论根底。
种子里有微小而奇妙的“胚芽”,被水滋润变成水草,生在水土间长成青苔,生在土堆变成车前草,车前草遇到粪土变成乌足草,乌足草的根化为金龟子,乌足草的叶化为蝴蝶。……羊奚草与不长笋的老竹结合,老竹又生出竹根虫,竹根虫生出豹子,豹子生出马,马生出人,而人又回到化生万物的造化之中。万物无不源自天地造化,无不返归天地造化。这里的“几”与“机”,是指天地、天人分化于混沌的机制或机关,有“自然”、“道”或“造化”之义,一如唐人孔颖达所疏:“几是离无入有、在有无之际,故云动之微也。”
从类似腐草化萤的观察中,庄子直觉地领悟到,世间存在原始的胚芽,由于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,变异成不同的生物种类,而且是循着由简单向复杂、由低级向高级的方向发展,所以,翦伯赞也认为“庄子的这一学说是伟大的”,“早在达尔文之前两千多年……就发表了他的进化论。”
《寓言篇》中,庄子说:“万物皆种也,以不同形相禅,始卒若环,莫得其伦,是谓天均。天均者,天倪也。”胡适认为,“万物皆种也,以不同形相禅”这11个字“竟是一篇‘物种由来’”!即万物同本一类,后来才以“不同形”“相禅”(“相嬗”,承继转化),从而一代代进化成万千的物类。
我们认为,庄子的进化观不是自大、傲慢的,而是忘我、平等的。万物相禅,开端与终结,有如首尾衔接的环,理不清次序。而这才是自然的均平之道。自然的均平,也是自然的差异。无论是“种有几”“万物皆种”,还是“万物皆出于机,皆入于机”,不外就是“齐物”与“天均”:人虽然是天地万物进化的顶端,但也不能妄为忘形。毕竟,“天地与我并生,万物与我为一。”
人与万物平等共生、利益攸关,这是一种普适、博大的生态情怀。后来,荀子在高喊“制天命而用之”的同时,不忘“草木荣华滋硕之时,则斧斤不入山林”,以实现“不夭其生,不绝其长”的可持续发展。
“种有几,得水则为㡭”,还有一层更深的寓意,即生命的进化是从水开始也是由水开启的,这样,由进化而来的世界自然具有水的韵味和品格。水,是老庄所偏爱以至崇拜的。上善若水,水有至德。水善利万物而不争,水滴石穿又天下莫强。顺应自然、忘物无为是水的本性;生命伦理、生态哲学,以水为宗,天人合一。
庄子是伟大的,他以无“机”之心领悟到“机”、把握住“机”,直觉地认识到生物的进化。但在精神态度上,庄子又是反人类中心主义的,对天地万物生出道德上的普遍关怀,敬畏之,友爱之,呵护之,赞美之:“天地有大美而不言,四时有明法而不议,万物有成理而不说。圣人者,原天地之美,而达万物之理。是故至人无为,大圣不作,观于天地之谓也。”自然,具有真善美圣的品格,寄托了庄子的求知、悟道、审美还有人格理想,一切的一切!
19世纪,“昆虫界的荷马”法国博物学家法布尔从杂草荒石中捧出一部《昆虫记》,感动了全世界:
“你们是把昆虫开膛破肚,而我是在它们活蹦乱跳的情况下进行研究;你们把昆虫变成一堆既可怖又可怜的东西,而我则使得人们喜欢它们;你们在酷刑室和碎尸场里工作,而我是在蔚蓝的天空下,在鸣蝉的歌声中观察;你们用试剂测试蜂房和原生质,而我却是研究本能和最高表现;你们探究死亡,而我却是探究生命。”
2300年前的庄子,为生命放声歌唱,为自然鼓满生机:
“虽然对动物有喜欢、有嘲笑,但庄子对之浑无恶意,更多亲切、平等的感情。庄子有一个广阔而繁盛的动物世界,既有鲲鹏、鵷鶵,也有斥鴳、鸠雀;既有虎豹狼狙,也有马牛龟蛇;既有螳螂井蛙,也有蝉蝶豕虱。他似乎喜欢独自漫游山泽林间,自小就因出身流亡家族而缺乏邻居伙伴,因而对林间百物是如此知根知底,知性知情,随手拈来,喻理证道,恰切、灵动而别有一番机趣。”
“机趣”,生命之“机”焕发出来的童趣,杨义先生可谓一语切中命门!
萧然物外,自得天机。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,《庄子》一书中有三处专门说“机”,而且分别应用了寓言、重言和卮言的不同手法,循着载道、得道和顺道的内在逻辑,环环相扣,浑然天成。
“机巧忘夫人心”与“机缄而不得已”,从反与正两方面论说忘物无我、无欲无为与载道、得道的关系。只有摈弃外在诱惑、清除内心欲望,才能顺应自然(“载道”),领会并驾驭“机”(“得道”),无为而无不为,以无“机”之心方得“机”之大用。
高歌着“机”的功能,南唐道士谭峭自信空前爆棚:
“转万斛之舟者,由一寻之木;发千钧之弩者,由一寸之机。……得天地之纲,知阴阳之房,见精神之藏,则数可以夺,命可以活,天地可以反复!”(《化书》)
比起与造物者游、与永恒为友的祖师爷庄子,谭峭并不算狂妄。爱因斯坦以童趣的好奇发现太阳和宇宙中所有恒星发光之“机”——质能关系式E=MC2,并制“机”而用,人类进入到原子能时代,天地翻覆也不再是狂想!
“万物出入于机”的顺道,是“机巧忘夫人心”的载道和“机缄而不得已”的得道在逻辑上的延展与升华。以无“机”之心获取的“机”之大用,在庄子看来,一定且必须是与自然平等、友好的。若因制“机”得“道”后而忘乎所以,私欲膨胀,傲倪于万物,驾自然而上,生杀予夺,肆无忌惮,这不仅失却了制“机”得“道”的初衷,而且也不可能制“机”得“道”,相反只会招来灾祸无穷。“天机不可泄露”,“德不配位,必有灾殃”,讲的就是这个道理。
“道”是抽象的,“机”则相对具体很多、活泼很多。可能正是如此,庄子不仅用“机”释“道”,而且将“机”喻“道”,从而完成了“独与天地精神往来,而不傲倪于万物”的个性张扬和人性解放!
作者分别为东华大学教授、博士研究生
主编:王多
 642
642 41.8万
41.8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