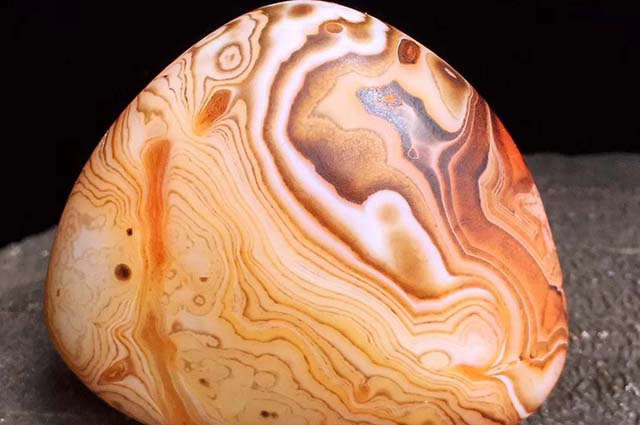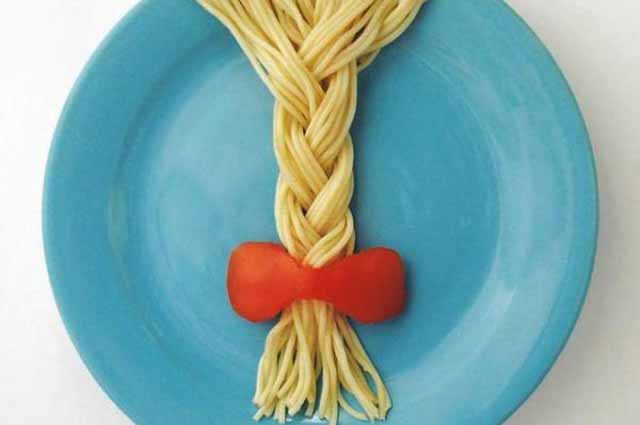语文教材,“连滚带爬”地读?
新近颁布使用的部编本《语文》,不仅大大增加了古诗文的篇数,而且进一步要求学生课外大量读书。这引发了人们的关注。不少人担心这是不是会加重学生的负担?

应该说,确实有加重学生负担的可能,但未必一定会加重负担。关键是怎样引导学生的阅读。对此,教材总编温儒敏提出一个有趣的见解:鼓励孩子“连滚带爬”地读。“不要每一本书都那么抠字眼,不一定全都要精读,要容许有相当部分的书是‘连滚带爬’地读的,否则就很难有阅读面,也很难培养起阅读兴趣来。”
这一说法,很有价值。“连滚带爬”地读,首先是读书时暂不去查字典,而是通过字词的上下文猜测这个字词的意思。温儒敏讲:“小学生认字还不多时,要读一篇文章或者一本书,不能碰到生字生词就查字典,可以根据前后文意思猜着那生字生词读下去,只要大致能读,就不要中断,最好一鼓作气读下去。这样才有读书的兴趣,也才读得快,读得多。想想,我们小时候读《西游记》等小说,不就是这样跳读、猜读的?”

读书确实需要“识字”,但有一些字暂时不认识,也并不妨碍读书。周谷城曾讲这样的话:“我们可以说,识字不是文字教育的基本,而且识字与读书在心理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心理过程,甚至于会相互冲突。因为读书重了解意义,识字往往斤斤于形音的认识。读书时太重形音,则读不快,甚至于不易获得全篇意义。反过来说,一篇文中或一本书中有若干字不识,只须大意可懂,尽可以不去管他,至于字的音不识更不重要,技术字的形记的清楚,也情有可原。”这是有深刻道理的。
特别是少年儿童的阅读,更需要保持一种强烈的兴趣,而读到一个不认识的字就马上去查字典,不仅阅读时时被中断,而且也体验不到“猜测”而发现的喜悦,读书的兴趣会大半消失。

跳读、猜读,这是温儒敏的经验,也是中国学人读书的共同经验。如作家冰心回忆童年读书生活时,讲过她读《三国演义》的情形:“我囫囵吞枣,一知半解的,直看下去。许多字形,因着重复呈现的关系,居然字义被我猜着。我越看越了解,越感到兴趣,一口气看完《三国志》,又拿起《水浒传》和《聊斋志异》。”
阅读确实是一个不断“猜测”的过程,凭借自己猜测到一个字的意思,会有喜悦之情,有成就感。人做一件事情,往往是不完全会做的时候更有兴趣。一本图书,待书中所有的字都认识之后再读,这已经是晚了!
允许读错,不计较错读几个字,以求取阅读的高速度、大数量,这是很聪明的做法。作家贾植芳讲到自己小学读书的情形时也说:“在进入高小时,一位同学从家里拿来一本石印本的绣像本的《封神榜》给我看,书里的字虽然许多都不认识,但书里的故事情节、人物命运、却大体看得懂,并且使我入了迷。也可以说,以此为契机,书开始对我具有吸引力,因此把读书变成一种生活需要,最终由一个山野的顽童变成了一个知识分子。”他也是在“书里的字”“许多都不认识”的时候,开始读这些书的。
钱谷融回忆小学读书时,说:“四书五经之类我没有什么兴趣,也读不懂,最能吸引我的自然是小说。不知怎的,我第一部拿到手的竟会是半文不白的《三国演义》……那时我大约正读小学四年级或五年级,看《三国演义》,自然也是似懂非懂。但故事情节是看得懂的,而且很有兴趣。”“读过《三国演义》以后,我对小说发生了极大的兴趣。就把家里所有的小说书,一部一部地找来读。那时也不能分别好坏,自然更不懂得选择,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。像《七侠五义》《施公案》《彭公案》《说岳全传》《封神演义》《野叟曝言》《金台平妖传》……等等,就都是小学里读的。”这也是“连滚带爬”阅读的一个例子。

这种情况,古人也早就有过。周作人讲,嘉庆时人郑守庭《燕窗闲话》中就写道:予少时读书易于解悟,乃自旁门入。忆十岁随祖母祝寿于西乡顾宅,阴雨兼旬,几上有《列国志》 一部,翻阅之,解仅数语,阅三四本后解者渐多,复从头翻阅,解者大半。归家后即借说部易解者阅之,解有八九,除夕侍祖母守岁,竟夕阅《封神榜》半部,《三国志》半部。这位学人初读《列国志》时“解仅数语”,但读着读着,就“解者渐多”,再从头阅读时,已是“解者大半”。
孩子只要多读,养成酷爱阅读的习惯,当初即使是读错了字,日后也会纠正过来的。据杨绛说,钱锺书小时候酷爱小说,“家里的小说只有《西游记》《水浒》《三国演义》等正经小说。锺书在家里已经开始囫囵吞枣地阅读这类小说,把‘獃子’读如‘岂子’,也不知道《西游记》里的‘獃子’就是猪八戒。书摊上租来的《说唐》《济公传》《七侠五义》之类不登大雅的,家里不藏。锺书吃了酥饼就孜孜看书,直到伯父叫他回家。回家后便手舞足蹈向两个弟弟演说他刚看的小说。”后来,钱锺书成为大学者,自然不会再把‘獃子’读如‘岂子’。当初虽然有的字错了。
“连滚带爬”地阅读,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读书方法,值得提倡。
来源:光明日报客户端
责编:王子墨
编辑:朱晓帆 王远方
来源:光明日报
 719
719 8.7万
8.7万